
《容成氏》中堯讓賢部分的簡序調整芻議
(首發)
孫飛燕
清華大學歷史系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·容成氏》中有關於堯求賢者而讓的記載, 按照整理者李零先生的編排🙍🏼♀️,這部分簡文如下[1]:
是以視賢:履地戴天,篤義與信,會在天地之間,而包在四海之內🫁,畢能其事,而立爲天子。堯乃爲之教曰:“自【9】入焉🎃🕖,余穴窺焉。”以求賢者而讓焉。堯以天下讓於賢者,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🚶🏻♂️。【10】
簡文“自入焉🤹,余穴窺焉”,李零先生認為講的是堯暗中考察賢者的行為🤟❗️。他的解釋是🎂♒️:“指鑿孔於牆👨👧,令試用者入其內,自外觀察之。”[2]但是這種理解有兩點可疑之處👬:首先🍤,“自入”從語法和文意上都難以講通🤘🏻。第二🚅🤵🏿♂️,這種考察賢者的手段,實在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。難道在牆上鑿一個孔,而堯通過小孔窺視被考察者就可以判斷一個人賢或不賢嗎👨🏭🧛🏽♀️?
實際上,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在於,簡10所謂“余穴窺”的“余”字並非“余”字,而是“宗”字,整理者對簡9和簡10的編排是錯誤的。該字字形如下👩🏻🦽➡️🦹🏽♀️:
![]()
“宗”🥟、“余”在楚文字中字形相近🫸🏼👨🏼🔧,尤其是該字上部恰恰不清楚🧑🏽✈️,所以整理者釋為“余”字👨🏼🌾🧙🏻♂️,學者均無異議。不過在《容成氏》其他簡中既有“宗”字:
![]() (簡41)
(簡41)![]() (簡46)
(簡46)
也有“余”及“余”作為偏旁的字:
![]() (簡25)
(簡25)![]() (簡27)
(簡27)![]() (簡29)
(簡29)
將該字與“余”及“余”作為偏旁的字相比較,可以發現其差別主要有兩點🦆👯:一是沒有“余”字最下的一撇🧎🏻♀️;二是該殘字的豎筆也沒有像“余”那樣穿過第二橫筆到達第一橫筆🤵♀️。因此,其字形應該還是與“宗”接近🐳。
孫偉龍先生在討論戰國楚文字中的“宗”、“余”二字時💇🏿♂️,指出二者已經容易混淆🧟♂️,既有寫法近似“余”字之“宗”,亦有譌近“宗”形之“余”。但他更進一步指出,具體到個體的書手,在使用“宗”、“余”二字時大多會有意加以區別⤵️♖。他列出在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1-5冊中“宗”、“余”二字同出的簡文五篇,現將其表引用如下:
|
篇名 |
宗字 |
余字(旁) |
|
《上博一·孔子詩論》 |
|
|
|
《上博二·從政》 |
|
|
|
《上博三·周易》 |
|
|
|
《上博三·彭祖》 |
|
|
|
《上博二·容成氏》 |
|
|
孫先生指出💪🏿,在五篇“宗”、“余”二字同出的簡文中,“宗”字不加羨符“丿”🧎♀️➡️、“口”🎲,“余”字則大多數都使用羨符“丿”、“口”,只有《容成氏》篇使用了一例沒有羨符的 “余”字。應該是書手為了區分“余”、“宗”二字🫷,才有意識地這麽做👮🏿。[5]
孫先生所言《容成氏》中沒有羨符的“余”字,正是我們討論的這個字。可以看出,五篇簡文中 “宗”、“余”二字界限井然有別⛺️📔,唯獨《容成氏》該字被認為是唯一的例外🍬,作為沒有羨符的“余”字處理🏕。筆者認為,這所謂的“例外”恰恰從反面證明該字不是“余”♟,而是“宗”字。也就是說在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 第一冊至第五冊中👎🏽,二字在同一篇簡文中沒有訛混🦸🏽♀️。
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,該字釋為“余”在文意和字形上都有問題,當釋為“宗 ”。這樣簡9與簡10的編連自然也就行不通了🚶🏻♂️。筆者認為🪑,簡 10應該上接簡31🚶♀️🧚🏿♀️:
孝唇(?)[6]🏄🏼♂️,方爲三俈🧖🏻,救[7]聖之紀🦝:東方爲三俈,西方爲三俈,南方爲三俈🕓,北方爲三俈,以越[8]於溪谷,濟於廣川👰🏼♂️⛹🏿♂️,高山登✶,蓁林【31】入焉🌂,宗(崇)穴窺焉,以求賢者而讓焉。堯以天下讓於賢者✧,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🚌。【10】
“宗”讀為“崇”,意為高✍🏻👨👩👦👦。穴指洞窟🚶♂️。古代賢能之士常常隱逸于山林藪澤巖穴之間:
《韓非子·說疑》:觀其所舉🛌🏻,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👨🏽💼,或在囹圄緤紲纏索之中,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。[9]
因此👨🏽🍼,文獻中常常用“巖穴之士”來指代隱士🙍🏻:
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:巖穴之士,趣舍有時若此。[10]
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上》🏃♀️: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🚱,則戰士怠於行陣🆕。[11]
簡文“高山登➰,蓁林入焉,崇穴窺焉”,即登高山、入蓁林👨🏽💻、窺崇穴,三句話句式整齊,與下句簡文“以求賢者而讓焉”相接文意順暢🧖🏿♀️,是形容求賢地域之遍及。其含義與上舉《韓非子·說疑》中“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”相同👨👦。再如《周易》小過卦:公弋取彼在穴🩴。帛書《二三子》引孔子的話說👨🏻🎨:“此言聲(聖)君之下舉乎山林![]() (畎)畝之中也🤸🏻♂️。”廖名春師認為“穴” 比喻民間山野,“公弋取彼在穴”是比喻明君求賢於野🐏,[12]這是非常正確的👮🏿♂️👮♂️。孔子所言“聲(聖)君之下舉乎山林畎畝之中”亦可與《容成氏》簡文相對照。
(畎)畝之中也🤸🏻♂️。”廖名春師認為“穴” 比喻民間山野,“公弋取彼在穴”是比喻明君求賢於野🐏,[12]這是非常正確的👮🏿♂️👮♂️。孔子所言“聲(聖)君之下舉乎山林畎畝之中”亦可與《容成氏》簡文相對照。
關於“方為三俈”的釋讀🚶🏻,學者意見有很大的分歧。[13]在各家說法中𓀗,董珊先生的意見最值得重視。[14]他舉《尚書·堯典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白虎通義·封公侯》、《說苑·君道》“十有二牧”為證👇🏽㊙️,認為這十二“俈”或即古書的“十二牧”,簡文是說每方設立三人以為帝王之輔佐🪨,深入四方民間以行政事🫴。[15]
《韓詩外傳》卷六第十七章[16]:
王者必立牧🙇🏼♀️🚝,方三人🧑🧑🧒🧒,使闚遠牧眾也。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💇🏻,有獄訟而不平其冤🕵🏿♀️,失賢而不舉者👩🏻🚀,入告乎天子。天子於其君之朝也,揖而進之🏓,曰🧑🏼🦱:“噫,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?如何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👨🏻🦱,有獄訟而不平其冤,失賢而不舉🍹?”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。遠方之民聞之,皆曰:“誠天子也!夫我居之僻,見我之近也,我居之幽,見我之明也🎪。可欺乎哉🙆♂️🧑🏼✈️?”故牧者所以開四門,明四目👨🏼🎤,通四聰也🚓。《詩》曰:“邦國若否🦮,仲山甫明之🩴。”此之謂也👨🏻🎤。
《說苑·君道》[17]🤱🏻→:
周公踐天子之位,布德施惠🙇🏻♀️,遠而逾明。十二牧,方三人,出舉遠方之民🅱️,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,有獄訟而失職者⏭💪🏽,有賢才而不舉者🌚,以入告乎天子🖲。天子於其君之朝也👨❤️💋👨,揖而進之☛,曰☝🏽:“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🅾️🔒?何其所臨之民🐲,有饑寒不得衣食者,有獄訟而失職者🍕,有賢才而不舉者也🤸🏼?”其君歸也,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😭👨🏿,百姓聞之,皆喜曰🫔:“ 此誠天子也,何居之深遠,而見我之明也!豈可欺哉!”故牧者,所以辟四門,明四目,達四聰也*️⃣。是以近者親之,遠者安之🧔🏻。詩曰👩🏿🎓:“柔遠能邇,以定我王。”此之謂矣🀄️🫢。
從《韓詩外傳》和《說苑》來看🥊,王者立十二牧🙋🏼,方三人。其目的是“闚遠牧眾”, “出舉遠方之民”🎫。“遠方之民”包括三種情況:一是饑寒而不得衣食者,二是有獄訟而失職者,三是有賢才而不舉者👩🏻🎤。《容成氏》說十二俈“越於溪谷,濟於廣川🤦🏿♂️🎃,高山登🧑🌾,蓁林入焉,崇穴窺焉”,其目的是“以求賢者而讓焉”,這正符合《韓詩外傳》和 《說苑》中的第三種“遠方之民”:有賢才而不舉者。雖然“俈”的具體釋讀目前仍然無法解決,但可以推測“方爲三俈”的目的是與求賢有關。這也為筆者簡31與簡10的編連提供了佐證。
[1]釋文為寬式👖。
[2]馬承源主編🔻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》258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🧝🏼♂️,2002年。
[3]5·21指的是第五簡第21字。
[4]該字為筆者所增🤦🏼♂️💲。
[5]孫偉龍🪷:《<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>文字羨符研究》100-101頁,吉林大學博士論文,2009年。指導教師🧑:李守奎🔽。
[6]晏昌貴先生認為該字與第八簡“於是乎始語堯”之“始”字和第三二簡“治爵而行祿”之“治”字絕類,讀為“慈”🎣🧔🏿。( 晏昌貴:《〈容成氏〉中的“禹政”》👩🏿🏫📲,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富达💁🏽、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: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》第363頁,上海書店出版社🙀,2004年)郭永秉先生讀為“始”。( 郭永秉:《帝系新研—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》45頁🪱,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8年)陳劍先生原釋為“唇”👐🏻,(《上博簡<容成氏>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》注14👳🏿♀️,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》第334頁),後在網上討論中放棄此說。
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howPost.asp?ThreadID=824)筆者認為🉐,該字左半字跡磨滅⛳️, 晏先生對字形的分析言之成理🦸🏼,但似乎也不排除是“唇”字的可能性🚣🏻♂️,此處暫釋為“唇”。
[7]整理者誤釋為“![]() ”,( 馬承源主編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》274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🖐🏿,2002年)陳劍先生首先改釋為“救”,( 陳劍:《上博簡<容成氏>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》,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》第 330頁)其說可從。
”,( 馬承源主編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二)》274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🖐🏿,2002年)陳劍先生首先改釋為“救”,( 陳劍:《上博簡<容成氏>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》,《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》第 330頁)其說可從。
[9]陳奇猷🧖🏻♂️:《韓非子新校注》976頁👨🏽💻,上海古籍出版社♙,2000年💏。
[10]〔漢〕司馬遷:《史記》2127頁🏋🏻♀️,中華書局,1959年。
[11]陳奇猷:《韓非子新校注》700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🫄🏻。
[12]廖名春↗️:《<周易>經傳十五講》147頁,北京大學出版社♛,2004年。
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 Src_ID=479)💂🏿♂️;或讀作“曹”,訓“輩”、“群”等🧓🏿。“為曹”即古書所見的“分曹”,是分班的意思。(大西克也:《戰國楚系文字中的兩種“告”字》,《簡帛》(第一輯)92頁👊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)。此外🍾,還有讀“聚”說(單育辰:《新出楚簡<容成氏>與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研究》54-55頁,吉林大學2008年“985工程”研究生創新基金資助項目。)
[16]許維遹:《韓詩外傳集釋》219-220頁🎪,中華書局,1980年。
-

水土 在 2009/10/19 14:30:18 评价道:第1楼
瞎說一下:「崇穴」似乎沒聽說過。冬侵二部的關係,近人已多言之。上博《周易》「朋盍簪」的「簪」⛹🏼♂️,從「琮」(陳劍說)🐇。因此,是否可以把「宗」讀為「潛穴」?查詞典,「潛穴」的詞例皆較晚。如果此說可以成立,則可見「潛穴」出現得並不晚。
-

yihai 在 2009/10/19 17:29:45 评价道:第2楼
也瞎説一下。
“ ”字第四筆(下半中竪上所接)明顯作弧筆而非直筆🦇,左右皆往上彎,與同篇“宗”字也可以說是有明顯區別。釋爲“余”恐難斷然否定。
”字第四筆(下半中竪上所接)明顯作弧筆而非直筆🦇,左右皆往上彎,與同篇“宗”字也可以說是有明顯區別。釋爲“余”恐難斷然否定。
“自入”即“自納”,意即“自己(向君上)推薦自己以求被接納任用”。匆促略檢古書🤽🏿♂️,其例如《後漢紀·光武皇帝紀》:“是时世祖在邯鄲🥅,(耿)純見世祖長者🏡,官屬齊肅,遂求自納焉。”《全晉文》卷四十八傅玄《通志》👩🏿🦱:“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🤦🏼♂️,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,則權移左右📠,而上勢分矣。”《全晉文》卷四十七傅玄《舉賢》🦘:“高祖勢尊而處高,故思進者難;蕭何勢卑而處下,故自納者易↘️。”《全晉文》卷四十七傅玄《義信》:“信者亦疑𓀂📢,不信亦疑,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✋🏽🎹,懷姦者飾邪以自納。此無信之禍也🧗🏻♂️。”《吳越春秋·闔閭内傳》:“(孫武)乃一旦與吳王論兵,七荐《孫子》。吳王曰:子胥託言進士🔯,欲以自納。”“自入”並非“從語法和文意上都難以講通”。
“余穴窺焉”似應理解爲堯親自窺視、窺求於賢者所隱居之巖穴,以發現、求得賢者(“以求賢者而讓焉”當也是堯之語)🤦🏻,似亦非不通。 -

海綿寶寶 在 2009/10/19 20:15:14 评价道👛:第3楼
我也搅和一下,若依作者读为“崇穴窥”👳🏿♂️,这所谓“崇高洞穴”只能“仰”,用“窥”是不合理的。
-

隨人 在 2009/10/19 22:08:28 评价道:第4楼
“穴”不一定是賢者所隱居之巖穴,也可能是墓穴🤜。又,“窺”也似乎不一定是采取俯視➕。司馬遷自云🫸🏻:“二十而南游江🙌🏻、淮⛱,上会稽,探禹穴👉🏽,窥九疑⛺️,浮沅🫱🏻👰🏻、湘。”“探”、“窺”互文見義,此句是否與《容成氏》有關亦未可知👿。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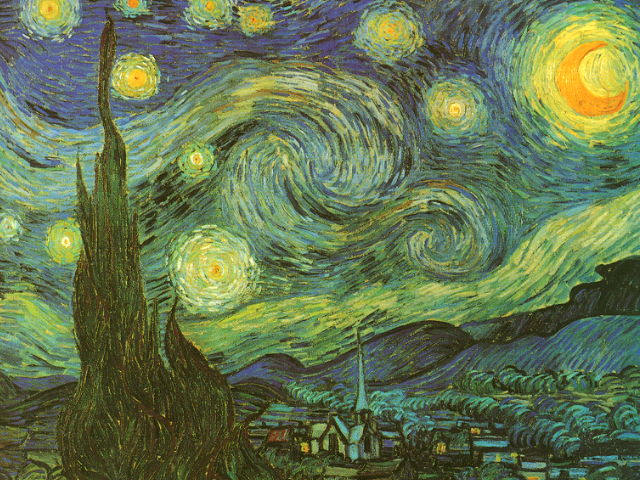
林文華 在 2009/10/21 16:32:10 评价道⛏:第5楼
也發表一些淺見:
原簡本作“自內焉”,陳劍先生疑“內”讀作“納”(參〈上搏簡《容成氏》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〉)📞🐹,“自納”古書多有其例,yihai先生所言甚是👩🏿🔧,此處讀作“自納”較“自入”為佳,指自我推薦🧑🧑🧒、自求見用🐎。
至於“余穴窺焉”的意思👎🏿,有兩種可能,第一種乃“自內焉”👌🏽、“余穴窺焉”為前後連貫之意,則“穴”字可能非字面之意義,而是“內”之通假,蓋“穴”、“內”古書多通用🧑🏼🔬,如《禮記‧月令》🦻🏻🧗:“蟄蟲咸俯在內”,“內”字《呂氏春秋‧季秋》作“穴”;又《韓非子‧八說》:“不若堙穴伏橐”,王先慎集解引盧文弨《荀子拾補》云𓀇⏱:“內🧝🏼♂️、穴古多通用”。至於“窺”也不一定解作俯視、竊視、暗中察看之意,也可直接釋作見之意🧑🏿🦲👟,如《呂氏春秋‧君守》:“而實莫得窺乎”,高誘注:“窺,見也。”又《呂氏春秋‧精諭》:“弗能窺矣”,高誘注:“窺🫰🏼,猶見🏊🏻♂️。”因此,簡文“余穴(內)窺焉”承上句“自納焉”,乃意謂堯於宮內接見自薦之賢者。
第二種乃“自內焉”、“余穴窺焉”為並列的 關係,而非前後相連意義,則“穴”字可能指巖穴,乃賢者隱居鄉野之處🍸,“余穴窺焉”意謂堯四處於巖穴鄉野探見訪求隱居之賢者。簡文“自內焉,余穴窺焉🥷,以求賢者而讓焉”,意謂堯告訴臣民不論是自納自薦者👮🏿♂️,或遠至巖穴鄉野探求者 😔,都是為了求取賢能之人而將帝位讓給他。
Copyright 富达平台 - 注册即送,豪礼相随!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84952号 地址✳️:富达注册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🧝🏽:200433
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
總訪問量:737549
 0526《容成氏》中堯讓賢部分的簡序調整芻議
0526《容成氏》中堯讓賢部分的簡序調整芻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