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(首發)
林澐
吉林大學考古系
琱生尊的釋讀
在上面討論的基礎上,我提出自己對琱生尊的釋讀如下🤦🏼♂️。
第一段🏃:
隹五年九月初吉🥿,召姜![]() (貽)琱生
(貽)琱生 ![]() 五尋、壺兩,以君氏命曰:
五尋、壺兩,以君氏命曰:
1、![]() :
:
![]() 在甲骨文中就常見🧃。過去常解釋為“致”。其實這個“
在甲骨文中就常見🧃。過去常解釋為“致”。其實這個“![]() ”應該解釋為“貽”或“詒”——這兩個字都是“送”的意思。《詩•天保》“詒爾多福”,毛傳:“詒😨,遺也📠。”《詩 •靜女》“貽我彤管”,釋文:“貽⛄️,遺也。一本作詒。”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 •言部》“詒🤦🏻♀️,假借為遺。”非是。詒、貽,之部;遺🧑🏼🦱,微部。
”應該解釋為“貽”或“詒”——這兩個字都是“送”的意思。《詩•天保》“詒爾多福”,毛傳:“詒😨,遺也📠。”《詩 •靜女》“貽我彤管”,釋文:“貽⛄️,遺也。一本作詒。”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 •言部》“詒🤦🏻♀️,假借為遺。”非是。詒、貽,之部;遺🧑🏼🦱,微部。
2🚶♀️➡️、

這個字現有六種解釋,我認為都有問題🙍🏼♀️。
陳昭容釋幭,王輝釋熾🧑🏼💻。吳鎮峰認為從斁聲,讀為緆👌🏼。他們的解釋與相應的古文字字形相差較大🌻🧑🏼🍳,都不妥👧🏻。
李學勤認為從烕聲,讀為幣。我覺得也不對。戈和火在一起🥵,不構成“烕(滅)”。說到“烕”🪗,我們要從下圖所引字形說起。下圖中兩字形,甲骨文中用作人名。于省吾1941年在《殷契駢枝續編》中釋為烕,認為是從火戉聲,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從之👞。後來于省吾先生放棄此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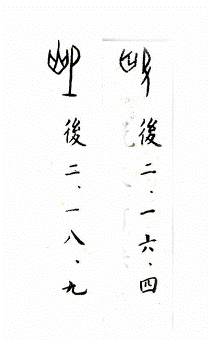
其實今天看來,它們並不是從戉得聲,而是從一扇形。從考古資料,如曾侯乙墓出土的資料看🎱,扇子都是一面的,與此形近。一直到漢代畫像石裏面人拿的扇子👨🏻🍼,也是這樣的形狀⛔️。這是個會意字,不是形聲字。有人說扇子只能把或越扇越大🐈,但其實以扇滅火也是可以的。“烕”字🛴,《說文》裏從“戉”,是由於字形的訛變🏇🏽。這個字和琱生器裏的字也是沒有關係的。從戈從火的不會是烕的。
我認為假如要和甲骨文聯繫🤸,字形可以聯繫上的是如下圖所示字👙:

此字甲骨文用為求雨的对象🔮。但具體何意不知。待考。
3🐘、

這個字應該釋為尋。這裏尋從巾,或許是因為它經常作為測量布帛的單位。有人認為是“帥”🐝,不妥。我們看如下一些字形🥽。“帥”兩只手方向一樣,而“尋”強調的是從一個地方伸出兩只手🏃🏻。再看尊中的兩個字💇🏽♂️,也是從一個地方伸出兩只手❇️。順便說一下💅🏽,何琳儀先生在《戰國古文字典》中認為“帥”從“尋”得聲,是把兩種字形混了,也是不對的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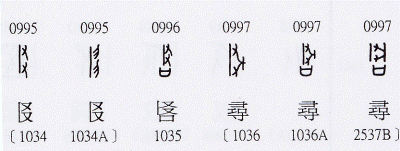
第二段:
余老之🪶,我僕庸土田多刺🟦。弋許勿使散亡🚺🙆🏼。余宕其三,汝宕其貳。其兄公👶🏿,其弟乃😈。
1‼️、之
于省吾先生在《詩經新證》裏就說過“止”是句末助詞,與“之”相同👆🏻⛹️♀️。這件器的“之”與琱生簋中的“止 ”相對‼️,說明于先生的說法是對的。朱鳳瀚先生《琱生簋銘新探》(《中華文史論叢》 1989/1)一文中詳細論證說:
止作為句末語氣詞多見於《詩經 •小雅》及《周頌》諸篇,如《小雅•采薇》:“薇亦作止”,“歲亦莫止” 。《杕杜》:“日月陽止,女心傷止,征夫遑止。”《楚茨》🎎:“神具醉止”🧏🏿🦸🏽♂️。《周頌 •閔予小子》:“夙夜敬止”。《良耜》😨:“荼蓼茂止”。……
這和于省吾先生的說法是一致的🥁。
不過還有人提出來,銘文中“之”和“止”是通的,因為銘文 “用之饗”的“之”寫成“止”。但是這裏銘文有點不太清楚,是否是止不一定。其中一件是有點的🐭,可能是“世”。但是讀作“用世饗”卻又沒有相同的句例🐡。我也沒有定論,這裏提出來🥌,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好的意見。
2、考
“考”,我曾經提出過讀作“老”。旁證是叔![]() 父器中,有“余考,不克御事”之語🤺,是說“我老了,不能處理事情了”。
父器中,有“余考,不克御事”之語🤺,是說“我老了,不能處理事情了”。
還要提出來說一下的是👰🏼,“余老止”是否可以念成“余考之” ?如果把之看成指示代詞,把“考之”講成調查、考察🌙,好像也是可以的。《詩•文王有聲》“考卜維王”🤳🏿,鄭箋:“考🥓,猶稽也。”《國語•晉語三》“考省不倦”🤚🏿,韋注🤟🏽:“考,校也👤。”《周禮•大司馬》“以待考而賞誅”,鄭注引鄭司農:“考,謂考校其功🤣。”但這樣沒有解釋為老好🤹🏿♂️,因為老和考是互相通的。這可以當作一個備用的解釋。
3😽、僕庸土田
這點在這裏我就不細說了。很多研究者認為,僕庸是指人,土田是田地,在座的裘先生也是持此意見🫶🏼。
但是陳漢平、王人聰等提出,僕庸是附庸,土田是指小國。他們的主要根據是,琱生簋中的庸是城墻的形狀。但後來發現的逆鐘💉☔️,裏面有“僕庸”,很明顯庸字不是城墻的樣子🍋🟩。說明它們不是一回事兒。金文裏沒有“附”寫成“僕”的例子🧑🚒。而且,金文裏有寫成城墻一樣的庸不能解釋為城墻的例子,如毛公鼎中的“庸”。所以我還是贊成裘先生的說法🧝♀️💂🏼♀️,將“庸”解釋為人。
4、弋
這個字,我支持裘先生的考釋意見。裘錫圭《史牆盤銘解釋》(《文物》1987/3):
“弋”是西周金文中常見的虛詞,《大系考釋》讀為“必”👩🏿🏫,按“必”🧎🏻➡️、“弋”古音不相近🕘,《說文》以為“必”字從“ 弋”聲,不可信👃🏻。用作虛詞的“弋”應該讀為《詩經》中常見的虛詞“式”,丁聲樹先生認為“‘式’者勸令之詞🌋,殆若今言‘應’言‘當’。”
5、宕
宕,我過去按《說文》解釋為“過”,就是“超額”。郭沫若釋為“放蕩”。陳夢家讀為拓,義為取。朱鳳翰認為“宕♛、當上古聲韻並同,當有承當、承擔之義”。現在看來,這些說法都不妥。我現在支持李學勤和王占奎的意見⛰,讀為“度 ”。
李學勤:和度均從石聲💂🏻,宕指度量。
王占奎:宅陰陽對轉🈺,宅度古通用🤷🏼♂️😕,宕就是居(占有)。
我認為王占奎的解釋比較好🚟。他引用![]() 器的銘文“宕乃子心”、“ 宕厥心”,以及文獻裏的 “維此王季,帝度其心。” (《詩•皇矣》)、 “維皇皇上帝度其心”(《逸周書 •祭公》)”,我認為都是對得上的。這裏“度”要解釋為“存在於他的心中”🐈,或 “占領了他的心”。度與宅古通用👳🏿♀️,宅和居意義也相聯繫。《詩•大雅》“宅是鎬京 ”,《禮記•坊記》引作“度是鎬京”。《堯典》“宅西曰昧谷”🧑🦼,《周禮• 縫人》注引書作“度西曰昧谷”。《詩•緜》“度之薨薨“毛傳;“度🗜,居也🐼。”《詩•皇矣》“爰究爰度”毛傳:“度,居也💆🏽♂️。”《呂刑》“何度非及”📎,《史記 •周本紀》作“何居非其有。” 現在成語裏如“居心不良”、“宅心仁厚”⏫⛹🏼♂️,居和宅都是一個意思。尊銘中敘述的事情是 “宕”土田僕庸,我覺得還是解釋為“占有”比較好。
器的銘文“宕乃子心”、“ 宕厥心”,以及文獻裏的 “維此王季,帝度其心。” (《詩•皇矣》)、 “維皇皇上帝度其心”(《逸周書 •祭公》)”,我認為都是對得上的。這裏“度”要解釋為“存在於他的心中”🐈,或 “占領了他的心”。度與宅古通用👳🏿♀️,宅和居意義也相聯繫。《詩•大雅》“宅是鎬京 ”,《禮記•坊記》引作“度是鎬京”。《堯典》“宅西曰昧谷”🧑🦼,《周禮• 縫人》注引書作“度西曰昧谷”。《詩•緜》“度之薨薨“毛傳;“度🗜,居也🐼。”《詩•皇矣》“爰究爰度”毛傳:“度,居也💆🏽♂️。”《呂刑》“何度非及”📎,《史記 •周本紀》作“何居非其有。” 現在成語裏如“居心不良”、“宅心仁厚”⏫⛹🏼♂️,居和宅都是一個意思。尊銘中敘述的事情是 “宕”土田僕庸,我覺得還是解釋為“占有”比較好。
6、其兄公🌊,其弟乃
兄,西周晚期時確實有加注注聲符作“![]() ”,這裏就不細講了。
”,這裏就不細講了。
對這句話的解釋非常多,我把我看到的一些說法列下:
王輝——“其兄公,其弟乃余”🦶🏼:哥哥就是公家,弟弟就是我
陳英傑——“其兄(貺)公其弟”🧝♀️;應該把它給予公的弟弟
辛怡華——“其兄(公)其弟”🕥:(因為你們)是兄弟關係
徐義華——“其兄公,其弟乃”🍸:兄長(召伯虎)繼承公爵🤦🏼,弟弟要擁護。
特別要說明一下,辛怡華的解釋是因為他認為“公”竄行了⚆🦸🏿♀️,他認為還有“止公”的🎅。
“乃”的一些解釋如下:
徐義華——乃通仍🧛🏽♂️🤵🏼,仍的意思是跟從、擁護。
陳昭容——《說文》“仍🤸🏼♀️,因也🎅🏽⚫️。”指因循。
李學勤——乃讀礽,義為福。
王占奎——乃讀為仍👨🏼🦳,仍通任🏄♀️。《周禮》鄭注“任,信于友道。”義為守信用。
吳鎮烽——乃讀為仍,《廣雅•釋詁》“仍,從也🕉👨🏿⚖️。” 義為服從。
但多數人還是認為,“公”是“公平”,“乃”是“因”。我也贊成這樣的解釋。還有一點補充的意見,我認為打官司的雙方是召族的兩支,所以有可能“兄”和“弟”不是具體指某個人是兄某個人是弟,而是指長房一族的和弟弟那一族👿。這樣解釋似乎更合理🙍♀️。當然這只是個初步的意見,還需要仔細考慮🔖。
召氏這一公族和琱氏因為土地問題發生糾紛👑,可能是由於歷史上的原因產生的一些糾葛。最後“君氏”出來調解。族長是最有發言權的🩷,族長說我占三份你占二份,這個事情才得以解決🐳。
第三段:
余熏大章🍋,報婦氏,帛束、璜。有司眔![]() 两墀。
两墀。
1、熏
這個字,本來我是念惠的👭🏻。這是受了郭沫若的啟發。郭沫若認為該字從黽,“即蟪字🙎🏼,讀為惠”🤿。![]() 的下面,我原以為是因為鑄造不好成此形🫢,原來應該是心🫸。現在還有人持此意見釋作惠🧎♀️。但是琱生尊出來后,很清楚,不應該是惠。下面應該是從黽的。上面這部分,與之接近的字形是“熏”。這個字上面是熏🫳🏻,下面是黽。
的下面,我原以為是因為鑄造不好成此形🫢,原來應該是心🫸。現在還有人持此意見釋作惠🧎♀️。但是琱生尊出來后,很清楚,不應該是惠。下面應該是從黽的。上面這部分,與之接近的字形是“熏”。這個字上面是熏🫳🏻,下面是黽。
 簋銘
簋銘 A尊銘
A尊銘 B尊銘
B尊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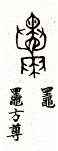 “ 黽”字字形
“ 黽”字字形
![]()
![]()
![]()
![]()
![]() 金文中“熏”字字形
金文中“熏”字字形
陳漢平認為該字下部從黽,上部從熏,或當釋為《正字通》所收的左蟲右熏之字🤸🏽♀️。並雲火煙上出為熏👳🏽♀️,香氣上蒸為薰👩🏼💻,吹氣上蒸之樂器為壎🛳🥼,酒氣上蒸為醺👯,天氣暖蟲復蘇而出為左蟲右熏之字🧕🏽。“凡從熏得聲之字,均有自下向上之義🦿。”銘文此字👩🏽🏫🏙,有自下向上奉獻之意。李學勤用陳說釋字🈁,認為此字曉母文部,“應以音近讀為明母文部的‘問’,《儀禮•聘禮》注:‘猶遺也🍜,謂獻也。’” 陳漢平的釋讀雖然在一些細節上不妥🤽🏽♂️,但偏旁分析是對的。我現在沒有其他的說釋法🙅🏻♂️🔫,只好用李學勤先生的讀法🕤。
2、![]()

這個字🍡,徐義華釋盥,認為是神靈見證儀式時表示誠信的盥洗或盥祭。王輝釋盥🛒👩🏼⚖️,認為是兩件盥洗用具。李學勤認為即錫字。我也沒有很好的意見,只是覺得有兩種可能👩🏽🏫,一種可能是“益”⛎,是“益”多出兩個手的增繁形體🛀🏻。如果是“益” ,則“益”在古文字中有兩個系統,一個是從幾點的,一個是從水的。以前從水的“益” 在金文中是沒有的。假如是“益”,勉強可以看作是金文中的例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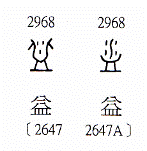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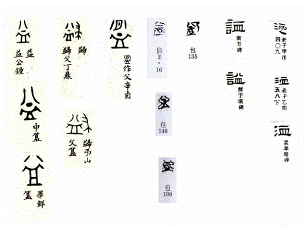

還有一種思路🧘🏽♀️,認為此字是“匜”的比較原始的寫法。金文中也有“匜”🤙🏻,但金文中都是從兩個器皿的。所以從字形上說不是很密合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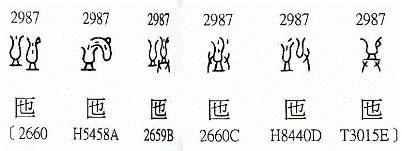

陳昭容隸定為上益下廾,認為有給予之義。他把益和匜看作一個字,這是引陳五雲說法,認為賜予和受益兩義相因🚈。這樣的說法也不太可靠。
所以🦋,雖然以上兩種可能都有❗️🍦,但我還是沒有把握確定到底這是個什么字。
3、

這個字👩✈️𓀓,陳昭容和李學勤釋辟🐰,以為指玉璧🔉❤️。但是這個字上面寫法和“辟”不同,它上面是從“尸”的🫃🏿👏🏽。金文中的“辟”不是從“尸”的🦸♂️。有個別有從 “尸”的“辟”,如![]() 簋,但這是寫錯了,因為只有一例。戰國時候字形訛混,兩種字形就不分了✌🏼,但西周時候應該是有區別的。有人會說毛公鼎和番生簋中兩個字指同一件器物🙋🏽♀️,是“尸”與非“尸”的字形相通的例子。我覺得其中一個字是鑄錯了🎥。這個字是說一種車馬器,具體是什么🙌🏻,沒有確定的答案。
簋,但這是寫錯了,因為只有一例。戰國時候字形訛混,兩種字形就不分了✌🏼,但西周時候應該是有區別的。有人會說毛公鼎和番生簋中兩個字指同一件器物🙋🏽♀️,是“尸”與非“尸”的字形相通的例子。我覺得其中一個字是鑄錯了🎥。這個字是說一種車馬器,具體是什么🙌🏻,沒有確定的答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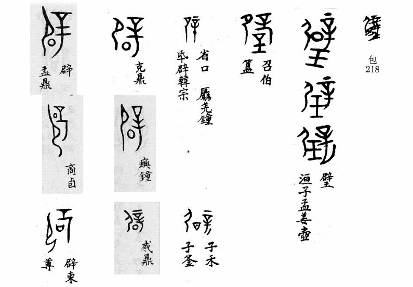
![]() 毛公鼎
毛公鼎  番生簋
番生簋
所以這個字應該是“屖”♦️。袁金平釋“屖”🎤,以為宰字異文。陳英傑🏋🏿、辛怡華釋“屖”,辛怡華以為“閒雅的”👠。徐義華釋“辟”,訓開,兩辟指雙方一同開視劑約或典法之書🙇🏿♂️,“辟法”🙇🏻🍠、“辟藏”🧛🏼。既然不是辟,而是屖👩🔧,屖犀同為心母脂部😺,可讀為墀🧍🏻♂️。《說文》“墀🔰,塗地也🪺。”又可指階。考古發現周代建築,階上往往塗有白灰面♥️。所以“塗地”和“階”兩意義是有淵源的🖲。“两墀”可能表示事情發生的地點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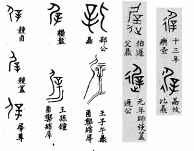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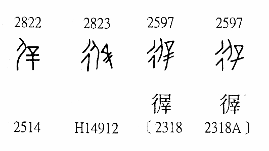
但“有司”後兩字不好解釋🤷🏿♀️。是不是說在向琱生傳達命令的時候,有司參加了?我覺得是有可能的🦍。整句話的意思我也不是很清楚。“熏大璋”是“熏 ”給誰呢👨🏻⚖️?我覺得可能是給君氏,因為前面講“君氏之命”,所以把“君氏”省略了🙆🏻♂️。也有人主張“惠大璋”不是送給某人具體的東西而是受某人的好處,但這個字是不是“惠” 也不清楚👱🏼,所以說法也站不住的🪁。
第四段:
琱生奉揚朕宗君休👀,用作召公尊䖒🙆♂️。用祈前錄、得(?)純,靈終🪯,子孫永寶用之享💾。
1、

這是器名。這個字是比較清楚的。上面是“䖒”。《說文•䖒部》“䖒,古陶器也👨🏼🏭。”這種陶器在西周是很普遍的,考古學界叫做大口尊——之所以把新出器物叫琱生尊就是這個道理。而且琱生尊的紋飾和陶器也是一樣的。辛村、周原都出這種陶器🏋🏼♀️。
陳昭容根據張家坡所出陶器,比較說這兩件銅器年代比較早。這個說法不妥🫃🏼,因為考古學界對陶尊的器物排隊並沒有確定💵,而且這種器物變化比較複雜,一時沒辦法總結其序列🖖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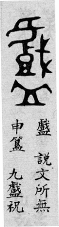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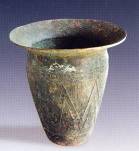 琱生尊A
琱生尊A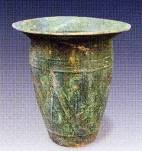 琱生尊B
琱生尊B
 天馬 -曲村M6382
天馬 -曲村M6382 M6080
M608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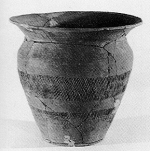 長安張家坡M197
長安張家坡M197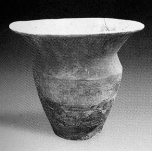 絳縣橫水M1
絳縣橫水M1
2、

這個字,好多人認為是“通”。理由就是![]() 鐘中的
鐘中的![]() 舊識為“通”。其實《金文編》把這個字收到“通”條是不對的。這是個壞字🪜,與已知的“通”不一樣。這個字上面的類似“通”上半環的部分,是“止”的殘筆。
舊識為“通”。其實《金文編》把這個字收到“通”條是不對的。這是個壞字🪜,與已知的“通”不一樣。這個字上面的類似“通”上半環的部分,是“止”的殘筆。

![]() 🤿、
🤿、 ![]() 、
、![]() 、
、![]() 等字形和
等字形和![]() 這樣的字形🧏♂️,見到的辭例都是一樣的💪。吉林大學何景成寫了一篇文章,還沒有正式發表,他認為這個字應該釋為“前”🐸。何文的觀點是,下圖所引諸字,已有研究者認為是“前”。這種寫法的“前”的中間部分可以簡化為兩橫一豎,這樣就與金文琱生尊中的字形相合了👱🏽♂️。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😌。何文認為前錄即戩祿,也就是福祿📉,似乎說得過去🥴。《詩•天保》“天保定爾,俾爾戩榖”,毛傳:“戩,福。榖,祿。”補充一下,甲骨文中的方國名
這樣的字形🧏♂️,見到的辭例都是一樣的💪。吉林大學何景成寫了一篇文章,還沒有正式發表,他認為這個字應該釋為“前”🐸。何文的觀點是,下圖所引諸字,已有研究者認為是“前”。這種寫法的“前”的中間部分可以簡化為兩橫一豎,這樣就與金文琱生尊中的字形相合了👱🏽♂️。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😌。何文認為前錄即戩祿,也就是福祿📉,似乎說得過去🥴。《詩•天保》“天保定爾,俾爾戩榖”,毛傳:“戩,福。榖,祿。”補充一下,甲骨文中的方國名![]() 🐍,與這個應該是一個字。(裘先生表示同意👰🏿🥝,並認為可能就是“湔”,是洗腳的意思。)
🐍,與這個應該是一個字。(裘先生表示同意👰🏿🥝,並認為可能就是“湔”,是洗腳的意思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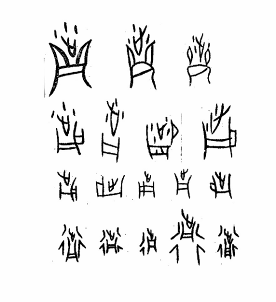
![]()
第五段🤛🏻:
其又(有)亂茲命,曰汝事(使)召人,公則明殛。
這最後一段,也是眾說紛紜,爭論很大🫡,我也沒什么好的意見,就不詳細敘述了。我猜想“公”是“召公”,就是他們的祖先。“其又(有)亂茲命” 是說如果亂了前面所說的君氏之命。“曰汝事(使)召人”🧚🏿♀️,是說本來這些人是屬于召氏公族的,現在已經明確了公族占其三,琱族占其二,如果不承認這樣的劃分,“使”了“ 召人”👩🏽✈️🧑🏿🎄,召公就要“明殛”——這是字面的意思🧑🏻✈️。
Copyright 富达平台 - 注册即送,豪礼相随!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84952号 地址:富达注册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:200433
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
總訪問量:706403